新闻网讯 4月27日,我校历史文化学院“史学名家系列讲座”通过腾讯会议APP成功举办。本次讲座邀请了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史睿副研究馆员主讲《唐代碑刻的物质性与文本性》,历史文化学院蒋爱花副教授主持。参加本次讲座的除本院师生外,还有来自日本、新加坡、台湾等地的学者、学生以及历史爱好者约300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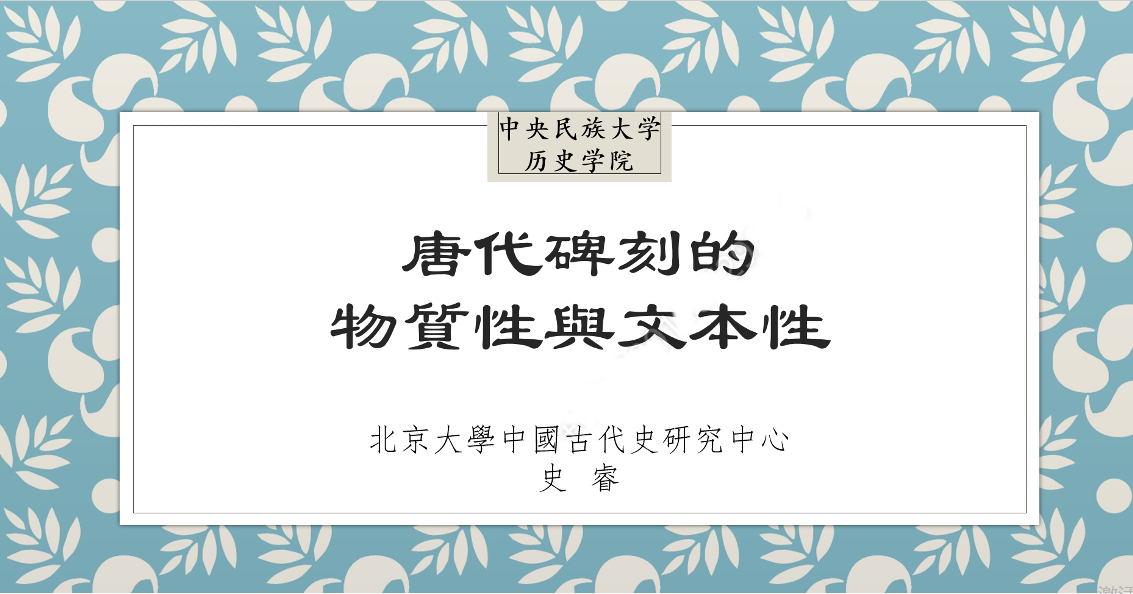
本次讲座以唐代碑刻为主要对象,从碑刻制作、传承、解读中的物质性与文本性介绍在碑刻这一具体史料研究中二者的交错现象。首先,史睿解释了文本性和物质性相关概念,在处理中古时期历史资料时,需要同时面对文本性与物质性两个层面;落实到具体的历史材料中时,从建立具体认知到纳入研究视野,需要进行的操作是十分复杂的过程。
史睿研究发现,唐代碑刻虽多,但是完整记载碑刻从碑文写作到碑刻制作、后世观看、传拓等历史过程的史料并不多,相对完备记载这一过程的是《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所记慈恩寺碑的制作史。通过对其内容的解析,可见唐代碑刻从文本落实到具体石刻的过程,印证了文本性和物质性交错的现象。
谈及书写这条线索,史睿表示在书写关系中存在着权力或者金钱的关系。至于权力关系,《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所记三藏法师强烈请求高宗亲自书写碑文便是很好的印证;至于金钱关系,史老师以张嘉贞、李邕和柳公权通过撰写碑颂获得丰厚报酬的例子来说明。接着,史老师又介绍了书写工具,根据日本奈良东大寺正仓院藏的毛笔、日本文献记载的毛笔及对比唐宋石刻书写和唐宋史料描述柳公权、王著书法作品,指出唐代碑刻文本书写形态独特,实为唐代缠纸笔的特点所致。
在镌刻过程中,唐朝较前代也发生了变化。史睿指出,唐以前由书写者直接撰写于石碑上然后进行刻字;入唐以后,此过程变为四个步骤,即在纸上书写、摹拓、摹勒(模勒)和刻字。如唐太宗书《温泉铭》、《晋祠铭》,武则天书《升仙太子碑》,玉真公主书《金仙公主墓志》,怀仁集王羲之书《三藏圣教序》及《三藏圣教记》,大雅集王羲之书兴福寺半截碑。以《升仙太子碑》为例,碑阴题字中更是直接出现了奉敕检校勒碑使、奉敕勒御书、刻御书等字眼。除此之外,他又用邵建和墓志所记刻工及其他刻工或作品,进一步解释了唐朝的碑刻镌刻工艺较之前已经发生改变,唐代刻碑匠人技艺相对提高。
史睿通过一组碑刻图片来让受众通过视觉直观感受碑刻完成后的情形,同时以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记》卷二对于王大尉墓堂保护情况的描绘、现代人对于升仙太子碑保护措施的照片来说明碑刻完成后会有相应的保护措施予以保护。史老师借胡仔《苕溪渔隐丛话》中引用的事迹,石碑修桥和向拱拓碑报答王溥,无意中毁坏田间庄稼,导致村民毁碑护田等,来说明人手可触及范围的唐碑会被破坏且屡有发生。同时,唐碑还会遭受其他形式的破坏。
虽然部分唐碑现已损毁,但是北宋开创的拓帖风气却使得这些碑文由碑入帖,从而保存下来。学界很少认为碑文会被收录到丛帖中作为代表作品,但是史睿把北宋《淳化阁帖》虞世南帖中文字和《孔子庙堂碑》碑文作对比,发现帖中内容实为碑文集字,从而追寻出了更多丛帖里有碑文的现象,是唐代碑刻传承中的变体。他引杜甫《李潮小篆八分歌》名句“峄山之碑野火焚,枣木传刻肥失真”,指出唐代已经开始了对于碑刻文本的传刻,以传其书法,保存真迹。化度寺碑敦煌本和原石本之间的差异,也可能成为唐朝已开始了碑文刻帖的有力依据。
史睿还介绍了复制碑刻文本的方式。一种是抄写,是唐代传播碑版内容的主要方式,如日本高僧圆珍的《行历抄》、《入唐求法总目录》中记载内容和越州诸暨县香岩寺经藏记(抄录本,敦煌藏经洞)等。另一种是传拓,最早的记录是《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文武三品已上表乞模打,许之”;窦暨《述师赋》窦蒙注“今见打本”。今所见最早拓本是唐拓本《温泉帖》(剪裱本,敦煌藏经洞)。同时,传拓方式也不是单一的,以《温泉帖》为代表的剪裱式和以《开成石经》为代表的分栏式,均可传拓。相较于剪裱式,分栏式可直接形成卷抽形态,可减少文本丢失和错乱。柳公权《金刚经》拓本中出现编号,不仅为后世帖式编刻提供经验,也表明了传拓技术的进步,从怀仁集王圣教序(金代)整幅拓本可以追溯其唐代起源。
史睿介绍了一起科学考古中发生的意外,即咸阳机场修建时窦希瓘神道碑被毁事件,以此建议考古工作者在进行科学考古发掘时,要扩大文物保护范围,保护文物免遭破坏。
他借用北宋李成《窠石读碑图》,引出观看石碑这种方式对于碑刻的解读受到很多客观条件限制,文本内容、文体也要面向不同的读者。
以欧阳修《九成宫醴泉铭》为例,复原此碑文需要考虑空间地理因素、环境因素,更重要的考虑是隋仁寿宫复原图。以赵睿冲神道碑碑阴所记为例,来说明复原碑文时还可以依据家族世系、兆域情况和撰写者何人等相关因素。随后,史睿讲解了验证复原是否正确的方法,以欧阳修《九成宫醴泉铭》为例,依靠的是列痕的连贯性、边部残损的整齐性。史老师通过对比罗振玉《昭陵碑录》和宋拓本之间存在的误差呼吁研究者在研究某一具体问题时一定要回归到原石或者善拓之中。
最后,史睿用《敦煌写本S.2078V“史大奈”习字之研究》和《敦煌写本北宋〈重修开元寺行廊功德碑并序〉习书考》介绍了用习字残存复原石刻较好的案例。
讲座结束后,蒋爱花用七个字谈及了对于史老师讲座的感受,史睿对于各种文献的深度挖掘,值得专注于某领域的学者学习,开拓新视野;他的讲座从分析到研究方法以及导致文本产生的周边因素,均有很高程度的解读;他对于各方面材料的熟悉度方面,造诣颇深。
在本次讲座直播过程中,著名碑刻学专家、洛阳师范学院毛阳光教授全程参与。在互动环节,毛阳光教授对本次讲座给予了高度评价:对于中古史研究,碑刻的大量出土提供了很好的契机。史睿对于物质性和文本性的讲解将有利于碑刻的综合性研究。学术界不能像以往一样只关注文本,文本解读必须考虑到物质的空间、时间、背景等因素,物质的研究能够对碑志的整理提供借鉴意义。通过物质与文本的交替性研究,能够对当下研究者深入研究中古碑志提供新颖的思路。同时,毛阳光也推荐了有助于更好吸收本次讲座的专题著作——《唐研究》(第二十三卷)“文本性与物质性交错的中古中国专号”。